《登春台》(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“中国好书”2024年3月推荐书目)是格非写下的第十部长篇小说,也是他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。步入“耳顺之年”的这位小说家,创作亦在越显宏阔的境界里,“登”上了一座别致的“坚台”。晴日里登高远望的去处,是古人的春台。不过,对格非的这部新作而言,“春台”一词特指“后厂村春台路67号”,是一个具体而精确的现代城市门牌。作者依据这一门牌号,在作品中筑基造厦,“神州联合科技公司”在这里顺利落成。通过“春台”这一空间意象,小说呈现出关于时代命题、命运格局和叙事手法的多重思考。
“神州联合科技公司”是一家提供物联网服务的私营公司。《登春台》的主体故事围绕着先后进入这里工作的四个人物徐徐铺开。通过这家“物联”企业,小说试图展现一幅从“物”到“人”彼此交错、紧密相连的时代图景。四位主角生于不同年代,长在天南地北,却被“神州联合”聚集一处,共同分享着“中关村软件园”和“后厂村”这一系列深含时代性的都市空间,也在这里听取到他者身上独具个性的生命故事。他们是社会发展历程的见证者,也是各自心灵遭际的倾听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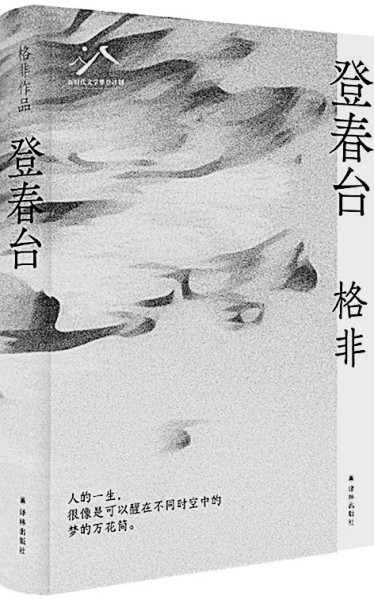
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出版
作为一位长于冥思的写作者,格非在现代社会纵横交错的多维联系网中,试图察觉出每个人之间心灵联系的内在真相。“联系性”可以说是格非写作时首先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。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,密布着比从前任何一个世纪都要繁多而平阔的马路,路上的数字信息准确定位着每一个地点。好比小说中富于标志性的“春台路67号”,若导航到这里,就可顺利找见“神州联合科技公司”和身处其中的沈辛夷、陈克明、窦宝庆、周振遐等主人公。顺着路的水平指引,获取的是他人的位置,却无法获知他人的内心,因为心灵没有门牌号码。在数智时代,人人都平等地拥有短短长长的几串数字,它们是门牌号、手机号或者证件号等。这些平整有序的数字固然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,却仍不足以讲述饱含情致与诗意的故事。
生命无法缺少故事。讲故事,正是使人们产生相互联系的重要手段。在有限的现实时空之中,故事扩展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视野,给予人面对生活困境的耐心和不断超越的信心。但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,现如今,遥不可及的“远方”早已经变为唾手可得的“附近”,包含丰富褶皱的“故事”也成了平滑的“信息”。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直言,讲故事就是对独异的个人经验的表达。中国作家木心给出的形容则更为生动,他认为地图是平的、历史是长的、艺术是尖的。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,《登春台》所表达的关切得以凸显:除了社会与历史所构筑的水平视角,对生活与人心垂直层面的探索与开拓,或许能让人们听见和说出更多的故事,生发出更深的联系。
格非筑造“春台”,继而又开辟“春台”的语义空间。小说若以“春台路67号”为书名,同样具有悬念。然而,“春台”与“春台路67号”之间所具有的微妙差别,正是这位作家的用意所在。作为一个精确的地址,“春台路67号”是四位主人公的交际场所和工作单位,它勾连起时代、历史和城市发展中其余的道与路。“春台”却可以被视为作品人物的内心空间和生命单位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台,观四方而高者。”凭借一个轻盈的跳跃,“台”凸显为听故事和讲故事的心灵高地。格非借“春台”揭示出世情和人心的基本图式:世人登台,除了远眺,更欲诉说。于是,“春台”由一个日常空间深化为一个“讲故事的地方”,如同穴居人温暖的火堆安全圈,也如同蒲松龄奇幻的聊斋空间。
《登春台》还勾勒出一种空间形式上的对称性:与“台”所表征的熙攘“高地”相对,小说还写到许多静寂的“低处”。人何以着迷于故事?《登春台》中是这么解释的:“人有一种将自己替换成别人,又将别人变回自己的愿望和能力。在想象中,我们不仅能够深切地体会别人的悲苦,也能分享别人的快感。”正是在“故事”的“听和讲”的过程中,小说的主角们觉察到自身的生命位置,它不在摇摇下坠的低处,也不在至高至上的顶点,它或许恰好是一个“春台”的高度。“春台”之上,故事之中,有人心的真联系,有人格的大潜能。
“春台”被塑造成一个“讲故事的地方”,得益于作家对汉语优美的空间性本质的感知与敬意。格非从“春台”的字面上看见某种高度,词语“春台”也在作者笔下获得某种厚度。学者赵奎英指出:“西方拼音语言是一种典型的线性语言,汉语言则具有某种空间化的倾向。”格非对此深有体会,他不仅关注“春台路”的时间性内容,更关切“春台”的空间性情思。李白有诗云:“登高望四海,天地何漫漫。”或者可以这么说:路,导向一种社会性的联系;台,则是天地间的融会贯通。
登临“春台”,人得以从低平的生活之流中超拔出来,以宽阔的心胸洞彻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。在“春台”维系的高度上,人可以寄托深心与远思,拓展精神视野,扩充思想容量,从而实现极目天地间的无限可能。
转自:光明网
